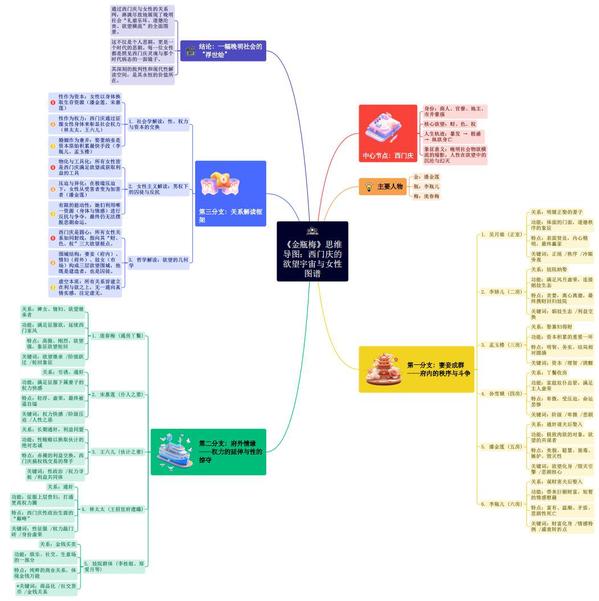一等奖
读《金瓶梅》:筷箸起落间的人性深境
教育学院 杜羽彤
初读《金瓶梅》时,身边同好总执着于书中描摹的情欲纠葛,我却在反复翻阅中,被饭席间筷箸的细微动静牵住了目光。这本常被视作市井世情录的著作,于我而言更像一柄以竹箸为刃的解剖刀——顺着那纤长筷身的起落,悄悄剖开了人性深处藏得最深的褶皱。
李瓶儿以鲥鱼设宴款待西门庆的章节,我至今记得读时的触动。象牙箸尖轻轻挑起那片细嫩如脂的鱼肉,筷身微颤的弧度里,藏的哪里是进食的寻常?分明是人心底的算计与欲念,借着这双筷子无声传递。兰陵笑笑生写饮食从无闲笔:酸笋汤入口的酸涩,恰如某些角色性情里的尖刻;酥油泡螺嚼在口中的黏腻,又像极了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人际牵绊。此时的食物早跳出了果腹的本质,成了藏着隐喻的符号,而筷箸,正是能解开这些符号的钥匙。
最让我难忘的,是西门府宴席上筷箸划出的等级界限。西门庆手握金箸,席间的山珍海味任他随意取用;仆役们握着粗竹筷,却只能在粗瓷碗沿打转,连靠近主桌珍馐的机会都没有。不过是一双筷子,却把那个时代的阶层壁垒刻得明明白白。后来春梅的筷子终于从下房的小桌,挪到了正厅的宴席上,这短短几寸的移动背后,是一个底层女子跨越阶层的惊涛骇浪。比起书中直白的议论,这双筷子的轨迹,倒更能让人看清那个时代的残酷真相。
随着阅读渐深,筷箸在我心里的意象也慢慢变丰富了。它有时像权力的影子,谁握着它给众人布菜,谁就攥着饭局里的话语权;有时又像欲望的触角,总往碗碟最深处探,想把最鲜美的那口抢到手;还有时候,它像块试金石,同桌吃饭时,是真心夹菜相让,还是假意应付,筷子的动作里全藏着答案。这几根不起眼的食具,倒比任何精密仪器都准,能测出人心底的温度。
合上书的那个傍晚,我望着桌上的筷子忽然愣神——我们不也和书里的人一样,手里都握着属于自己的“筷子”吗?如今的社会像一场盛大的宴席,我们的筷子该往哪里伸?是学西门庆那样,见着好的就往自己碗里揽,还是能守住分寸,留几分清醒?日子越过越富足,可人心底的困惑从没变过:到底该怎么在想要和克制、索取与付出之间找到平衡?那根看不见的“筷子”,还在悄悄试探着每个人的本心。
《金瓶梅》最难得的,从不是辞藻的华丽,而是它从不居高临下地评判。它就像个安静的旁观者,让筷子自己起落,让宴席自己展开,不添一句说教,却把人性的复杂全摆在纸上。作者用近乎冷静的笔触,记下筷箸间漏出的人心,这种不加修饰的白描,比任何道德议论都更有力量。我总忍不住想,兰陵笑笑生或许就站在时光的角落里,看着这一切,把故事写下来,不褒不贬,只等着后来的人,在字里行间读出自己的滋味。
其实仔细想想,一个时代的人情冷暖,从来都藏在这些日常的小事里。筷箸一落一起的瞬间,饭桌上的热闹与冷清、人的得意与卑微,全清清楚楚。这大概就是《金瓶梅》留给我们的启示:历史从不是只有宏大的叙事,更多时候藏在一粥一饭里;人性也从不在经书的教条里,而在每一次拿起筷子、放下筷子的犹豫与坚定里。
若能从这样细小的器物里,读懂人心深处的秘密,才算真的读懂了这本奇书,也读懂了这世间的复杂与真实。
《金瓶梅》读书心得
文化与传播学院 陈维耀
《金瓶梅》是中国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白话世情章回体小说,被誉为中国古典现实主义小说的巅峰,可见其价值远不止于对世俗情欲的描摹。
书名中“金、瓶、梅” 三字,表层上是取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性名字中的一字,深层上是世俗欲望的三重符号:“金” 即金钱,是书中世俗关系的 “硬通货”:西门庆发家始于生药铺,靠贩卖药材积累第一桶金后,又通过放高利贷、勾结官府买官敛财。他曾花费重金贿赂蔡京,得以谋得 “理刑千户” 一职,疯狂敛财;潘金莲也深谙 “金钱” 的重要性,甚至到对下人吝啬,对富人嫉妒。她克扣丫鬟月钱、觊觎李瓶儿的巨额嫁妆,甚至在西门庆死后试图卷走财物,金钱成为她争夺地位、维系生存的关键。
“瓶” 代表酒,而酒在书中是欲望的 “催化剂”:西门庆常与应伯爵等狐朋狗友在家中设酒局,酒过三巡便暴露贪婪本性,或商议敛财手段,或调戏家中妻妾;李瓶儿嫁入西门府后,每逢节庆或家庭聚会必有饮酒场景,她与西门庆的情感升温、与其他妻妾的暗流涌动,多在酒桌旁上演,酒既是世俗应酬的媒介,也助长了情欲与纷争。
“梅” 代表女色,呼应书中以情欲为核心的人物命运:庞春梅从西门府的丫鬟起步,因貌美被西门庆宠幸,后凭借与周守备的私情跻身权贵夫人行列,却始终困于女色之中。她与陈经济私通,甚至在成为守备夫人后仍纵欲无度,最终因情欲过度而亡;此外,书中诸多女性角色的命运皆与 “女色” 绑定,潘金莲靠美色吸引西门庆,李瓶儿因容貌被多方争夺,女色成为她们改变命运的筹码。
若说《红楼梦》构建了“大观园诗画世界”以诗词雅颂、园林景致包裹,写尽 “情” 与 “美” 的幻灭;《金瓶梅》则描绘了一幅 “清河县世俗浮世绘”,剥离所有理想滤镜,直面市井生存的现实。两者描绘的世界差异鲜明的两个世界:《红楼梦》的空间是封闭的世外桃源,宝黛是精神契合的凄美爱情,里面讲述的悲剧是诗意理想随着大家族的没落一齐倒塌;而《金瓶梅》的清河县是开放的市井生活,西门庆算账本、妻妾争厨房,人人被 “利”驱使,讲述的悲剧是欲望反噬的必然。西门庆纵欲亡故后,家产被分、妻妾离散,恰是世俗贪婪的终极代价。书中无 “螃蟹宴” 的雅致,只有蒸饺、黄酒的烟火气;无 “葬花吟” 追求自身洁白无垢的浪漫,只有放高利贷、行贿受贿的势利的现实,全然是 “饮食男女” 的生存本相。
其文学语言与气质更具生活气息。《金瓶梅》以“市井白话” 为骨,鲜活得仿佛能闻见清河县的烟火:潘金莲骂丫鬟 “小蹄子敢藏主子东西”,西门庆与伙计算药材利润,直白粗粝却贴合身份。更难得的是作者 “冷眼旁观” 的叙事方式。作者不褒贬、不抒情,仅记录西门庆的荒淫、潘金莲的狠毒、春梅的兴衰等,让读者自由去评判。这种 “零度叙事” 的冷峻,不同于《红楼梦》的诗意感慨,更具冲击力。《金瓶梅》不提供理想,却以最真实的笔触,揭示了“饮食男女”生存。
豪华去后行人绝,箫筝不响歌喉咽。
雄剑无威光彩沉,宝琴零落金星灭。
玉阶寂寞坠秋露,月照当时歌舞处。
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灰。
计算机学院 李国培
时光已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春风又吹红了花蕊,你已经也添了新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认为“金、瓶、梅有其隐性含义:血色、囚笼与虚无。这三个字,是书中三位女性的一生,也是一曲华丽的挽歌。
金(潘金莲):这“金”是烫手的,是血色黄昏的光。它不仅是她的姓氏,更是她一生悲剧的根源——她的价值被物化,如同一件可以估价、买卖的金器。她追求“金”(财富、宠爱),用尽手段想牢牢抓住,却最终被这黄金的枷锁烫得体无完肤,直至毁灭。这“金”,是欲望灼人的光芒,也是杀死她的凶器寒光。
瓶(李瓶儿):这“瓶”是她最美的写照,也是她最深的囚笼。她如同一只精美而易碎的花瓶,内里承载着对温情与安稳的极度渴望。她将情感与财富一次次寄托于男人(花子虚、蒋竹山、西门庆),如同将水倒入漏瓶,终是一场空。当她终于得到西门庆一点真情,生下官哥儿,这“瓶”似乎被填满了,但转瞬之间,子死、心碎、人亡。这“瓶”,最终碎得一地凄凉。
梅(庞春梅):这“梅”是三者中最具反抗与悲剧双重色彩的。她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原是丫鬟,却有着寒梅般的傲气与烈性。她不认命,用尽一切手段向上攀爬,从奴婢到守备夫人,看似实现了阶级跨越。但这“梅”花开得再艳,也根植于腐烂的土壤。她的欲望和骄傲最终在放纵中燃烧殆尽,死得荒唐又惨烈。这“梅”,是在凛冬强行盛放后,必然的凋零。
书名这三个字,合起来是一幅图:金色的花瓶里,插着一支注定要败的梅花。极尽奢华,却无生命根基,终将一同腐朽。这是对书中所有浮华世界最精妙的隐喻。
从作者的视角看:在深渊里看见人性的星光
作者绝非简单的道德批判者,他是一个深沉的悲悯者。他冷静甚至残酷地描绘出每个人如何被自身的欲望和时代的洪流裹挟着坠入深渊,同时又让我们看到深渊中曾闪烁过的人性微光。
潘金莲:我们恨她毒辣,但作者也写了她被当成物品一次次交易的悲惨前史。她的聪明伶俐在那个女性毫无话语权的世界里,扭曲为争宠害人的伎俩。她的疯狂,何尝不是对命运的一种绝望反击?她死时尸首无人收殓,何其惨烈,作者笔下满是苍凉。
宋蕙莲:这是最令人心碎的角色。她轻浮、虚荣,但作者也写了她天真烂漫的一面。当她得知丈夫来旺被陷害,她的觉醒和反抗是全书最耀眼的光芒之一。她用一条腰带自缢殉情,完成了从“玩物”到“人”的悲剧性觉醒。作者给予这个“坏女人”最壮烈的结局,其中悲悯,力透纸背。
庞春梅:她骄纵、狠毒,但对潘金莲,她始终保有一份罕见的忠义和情分。在潘金莲最落魄时,只有她去祭奠、收尸。这份复杂的情感,让她超越了简单的恶人标签,形象变得立体而可叹。她的命运,是对“心比天高,身为下贱”最深刻的哀悼。
作者仿佛在说:看,这就是滚滚红尘。他们都有罪,但他们也都不幸。我写下他们的沉沦,心中亦有无限凄凉。
《金瓶梅》的世界:不是“诗”,而是“生活”本身
如果说《红楼梦》是唯美的、悲剧的诗,是“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的理想世界;那么《金瓶梅》就是粗粝的、残酷的生活本身,是“人欲横流”的现实人间。它写的是一个“烟火人间”。 充满了生老病死、柴米油盐、算计斗殴、市井喧哗。它的语言泼辣、鲜活、生动,大量运用市井俚语、歇后语,充满了活色生香的生活气息和扑面而来的真实感。它的最大气质是“冷”。 作者像一个冰冷的手术刀,精准地解剖着社会的肌体,不加粉饰,没有滤镜。这种“冷”背后,是一种深刻的绝望和虚无——看透了繁华背后的肮脏,热闹之后的荒凉,所有欲望终将成空。这是一种“悲凉到骨子里”的气质。
《金瓶梅》里的世界,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反而像一面镜子,照得我心惊肉跳。对财富与权力的追逐: 书中官商勾结、贿赂公行的现象,在今天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西门庆式的“成功学”——通过金钱和关系打通一切——仍是部分人心中的潜规则。在物质丰富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像西门庆一样,陷入“买买买”和“纵欲”的循环,用物质的填充来掩盖精神的空虚,最终导致身心俱疲。我觉得《金瓶梅》对我的启示是,人不能被物欲异化, 追求更好的生活是动力,但沦为欲望的奴隶,终将失去自我。法律与道德的边界永远不能模糊,一个社会如果默许甚至崇拜西门庆式的“成功”,将是巨大的危机。在快节奏和充满诱惑的时代,更需要强大的内心和正确的价值观来定航,否则很容易在欲望的海洋中迷失方向。《金瓶梅》的伟大,就在于它毫不留情地揭示了这份人性的复杂和社会的真相。它不提供答案,它只呈现问题。它逼着我们去看,去思考,我们该如何面对内心的欲望,该如何自处于这个复杂的世界。
辨“万恶淫为首”之义
文化与传播学院 赵钰珊
我们常常会听到“万恶淫为首”这句俗语,我们一听到这个“淫”字,就很容易联想到男人和女人之间不道德的关系。同样的,一提到《金瓶梅》,我们又快速地给《金瓶梅》扣上“污秽之书”的帽子,一部上不得台面的书。《金瓶梅》是一部好书,由于大部分人只看到里面的性,说它是淫书、不值得一看的书。假如我要为《金瓶梅》叫屈,我应当就从“万恶淫为首”论起来,只有了然了这个“淫”的真实含义,我们才能看见《金瓶梅》的血、肉、灵。
“万恶淫为首”是真的吗?“淫”字的含义,通常我们以为的淫是指色,但从古代汉语的语义层面进行剖析,古代的“淫”并非淫邪之意,更倾向于指贪得无厌的欲望。例如,《孟子·滕文公下》中云“富贵不能淫”,《论语·八佾》中云“《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以,用现代的话来说,应是“万恶贪为首”,即在万般罪恶中,贪婪是最邪恶的。
世情小说《金瓶梅》是一幅工笔画,欲望之门大开,以西门家荒淫腐化为主线,写出了丑态百出的众生相,贪欲便是一切的万恶之首、万恶之源。
其一,看潘金莲被激情挑拨的贪欲。千秋万代,西门庆和潘金莲都头上顶着“奸夫淫妇”的帽子,我们且细看潘金莲的来时路,当潘金莲还是“武大家的”,面对一众狂蜂浪蝶,潘金莲也只是隔着帘子露着金莲小脚挑逗着戏弄着男性的欲望,并无出格、背德。此后,在等待西门庆的三个月里,同样没有生事。再后来,借王婆的说技,潘金莲又遇西门庆,激情死灰复燃。到了西门庆留在李桂姐那儿仅半个月不在家时,她就与年轻的小琴童通奸了,潘金莲的行为动机并非独守空房、淫欲之心可以解释。书中一言以道破:“丢的家中这些妇人都闲静了。别人犹可,惟有潘金莲这妇人,青春未及三十岁,欲火难禁一丈高。”而在后面的情节中,被赶出西门家的潘金莲仍选择和王婆的儿子厮混。因此,我们不能如此简单就认为她是个淫荡的妇人,她行为上发生的转变,映射的是她的心里那一团被激情挑拨的贪念欲火。
其二,看媒婆们的贪欲。由于这是一个“金童玉女”难相遇的社会,想要千里来相会,故事的开端就得依靠“唇枪惯把鳏男配,舌剑能调烈女心”的婆子丫鬟们。从王婆的处心积虑撮合潘金莲、西门庆苟合,再到薛媒婆说娶孟三儿,媒妁殷勤,无利不往。她们凭借一张巧嘴编织情网,牵头做淫媒为生,甚至“做马泊六,也会做贝戎儿”,昧着良心图利。这都体现了,在封建社会中,婚姻不仅仅是情投意合的事情,更是家族之间的一种联姻和利益交换。
这部“假托北宋,实写明朝”的世情小说实为好书,写尽了市井烟花巷的声色犬马,是整个社会奢靡淫纵百态的生动写照。人性复杂,这其中的“淫”也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单纯的色欲问题,它的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往往不如贪欲来得广泛和深远。对于“万恶淫为首”之语,我们应明辨其真义,辨其今误,以“万恶贪为首”正视听。我们不应该把《金瓶梅》斥为“淫书”而避之不及,不能放任具有重要文学价值和历史意义的作品长期被埋没在历史尘埃里面,只有摒弃偏见,用理性、平和的态度去欣赏这部作品,才能探寻到这部作品无尽的文学魅力。
文化与传播学院 胡碧纯